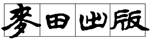三、第一次鄙視
我的腦中立即閃過了書上看來的對獒的印象:藏獒頭大而方,額面寬,眼睛黑黃,嘴短而粗,嘴角略重,吻短鼻寬,舌大唇厚。頸粗有力,頸下有垂,形體壯實,聽覺敏捷,視覺銳利,前肢五趾尖利,後肢四趾鉤利,犬牙鋒利無比,耳小而下垂,收聽四方資訊,尾大而側卷。全身被毛長而密,身毛長一-四釐米,尾毛長二-五釐米,毛色以黑色為多,其次是黃色、白色、青色和灰色,四肢健壯,便於奔跑,動如豹尾,搏鬥助攻,令敵防不勝防。一隻純種成年藏獒重六十公斤左右,長約四尺,肩高二尺半餘,強勁凶猛,即使休憩,其形凶相,常人絕不敢靠近。藏獒力大如虎,足以使一隻金錢豹或三隻惡狼敗陣,凶狠勁鬥,使之贏得神犬美譽,也是世界上唯一敢與猛獸搏鬥的犬類。
這些資料像電腦掃描圖層一樣從我的腦細胞中一一閃過,然後過濾、核對,最後得出結論,這是一隻絕對純種的獒!
「你是肖兵吧?」聽見獒的吼叫聲,多吉大叔從屋裏走了出來,不用多問,這一身軍裝就證明了我的身分。我是黑子在多吉大叔面前提起的唯一一個部隊裏的戰友。
黑子是個苦命的人,父母離異,從小跟著外婆生活,外婆死後,便隨著母親遷居到北京,在那段無憂無慮的童年生活中,多吉大叔成了黑子最親最近的親人。多吉大叔把黑子當自己的親侄子一樣看待,所以對我也就格外的親切,很熱情地招呼我進屋裏坐。
屋裏的擺設很簡單,雖然現在藏族同胞也都自己蓋房子了,許多已經脫離了隨牧草而遷徙的帳篷生活,但還是保留了不少藏族人民獨有的生活習慣。
我在寬大的地氈上盤膝坐下,黑子曾經告誡過我,藏族人有許多忌諱和規矩,坐的時候,一定要盤腿而坐,絕不能把你的兩隻腳底板對著別人,我知道藏族朋友的強悍不是普通民族能相比的,所以也就格外注意。
多吉大叔呵呵地笑了一下,給我端來手抓羊肉和酥油茶,還有藏族朋友們獨製的烤餅。差不多快兩天了,我開始慢慢適應高原氣候,所謂的高原反應也在慢慢消失,早上沒吃什麼東西,現在感覺到很餓,我大把地抓著鮮嫩的羊肉,美美地吃起來。看著我吃得狼吞虎嚥,多吉大叔笑呵呵的,在藏族朋友們面前,狼吞虎嚥並不算失禮,反而是粗放豪邁的一種體現,那種細嚼慢嚥的吃法卻是令人鄙視的。
我不明白,為什麼大黑站在門口要用一種極端鄙視的目光看我,她是那樣的高傲,像一個皇后,我卻彷彿成了在她面前乞食的奴才,我有一種受傷的感覺,在大黑那咄咄逼人卻又十分冷漠的目光之下。
多吉大叔自言自語起來,在我聽起來,卻彷彿是對我的一種安慰,他吸著一袋旱菸,說:「大黑是我一手養大的,抱回來的時候,她還在吃奶,家裏沒有別的獒,只能餵羊奶給她喝,大黑很喜歡和羊們親近,家裏的那群羊也都喜歡圍著大黑跑。」
我不得不承認,大黑有一個肥碩而強健的屁股,我想把她推開,但是又不敢,摸了驢屁股,驢還要尥橛子呢,何況是一隻凶猛的獒。
大黑像尊雕塑一樣矗立在門口,令我可望而不可及,我似乎很不招大黑待見,她根本連再看我一眼都不屑回頭。然而,黑子所說的話一直在我的頭腦中保留著深刻的印象,就是大黑對我這樣帶著歧視的冷漠,更激起了我想了解她的衝動。
天色慢慢地暗下來,落霞像姑娘頭上的彩色絲帕,被草原上的一陣風吹走了,大黑欣賞完美麗的夕陽,終於緩緩掉轉過她的屁股,邁著步子,走到多吉大叔身邊,在不遠處的一塊紅地氈上臥下。
那是一塊為她特製的精美的紅地氈,很漂亮,這令大黑更有一種無比的優越感,在我這個陌生人面前。
多吉大叔最小的兒子格桑放羊回來了,本來格桑是要帶大黑去的,因為多吉大叔早聽說我要來,所以就把大黑留了下來。格桑還小,才十三、四歲,臉蛋子上兩團高原紅,純樸得可愛。
四、狼來了
我把格桑叫過來,捏捏他的小臉蛋,他憨厚地笑著,從頭到腳地打量我,怯怯地用藏語問:「叔叔會使槍嗎?會打狼嗎?」
問過多吉大叔之後,我才聽明白,我笑起來,讓多吉大叔幫我翻譯,告訴他:「我管你爸爸叫叔叔,你應該叫我大哥才對。大哥以後會教你打槍,但是,你有槍嗎?」
格桑聽明白之後,忽然跑開了,過了一會兒,不知從哪裏翻出一支土制的獵槍來,緊緊地抱在懷裏,跑到我面前,遞給我看,槍桿子幾乎要高過他的頭。看著他認真的樣子,我和多吉大叔都大笑起來,多吉大叔告訴我,這支獵槍是他很久以前的東西了,那時家裏還沒有養獒,因為窮,養不起,僅有的幾隻羊是家裏最值錢的財富,為了保衛自己的財富,所以從一個獵人手裏買下了這支槍,現在,這支槍都已經生銹了,也不知道還能不能再用。
我笑著把格桑摟在懷裏,捏了捏他通紅的小臉蛋,看見我這個沒有絲毫地位的陌生人和格桑親近,大黑有些不悅,她低低地吼了兩聲,提醒我,不要忘了自己的身分,我有一種時刻要被她驅逐出境的感覺。畢竟,我現在是待在她的地盤上,我不得不看著她那陰沉的臉色。格桑似乎也有點怕大黑,不大和她親近,反而更願意偎在我身邊,聽我講部隊裏的故事,多吉大叔坐在旁邊,一邊捲他的菸葉,一邊當業餘的翻譯。
天晚了,格桑在擦那支生了銹的槍,擦得很仔細,也不知多吉大叔是怎麼和他翻譯的,他擦了一遍又一遍,連飯也忘了吃。
我看見大黑坐在她獨享的紅地氈上,威風凜凜地看著我們用餐,為了討好她,我把手上的一塊嫩羊肉遞了過去。大黑很不屑地從鼻孔裏噴出兩股粗氣,然後衝我齜了齜牙,意思是要我縮回自己的手。
多吉大叔只得告訴我,大黑不吃生人給的食物,而且,她從來不吃熟食。因為在獒們的眼裏,牠們天生就是大草原的寵兒,你給她吃熟食,她就會認為你這是對她的一種鄙視,凶猛的獒還會認為你這是在向牠挑釁,但大黑不會,因為她有良好的教養。
教養?我很吃驚。
多吉大叔笑了一下,解釋說:「這是天生的,純種的獒並不是人們所理解的那樣凶蠻而沒有理性,相反,牠們很高貴,有氣質,根本就不屑理會那些不知所謂的挑逗。」我訕訕地縮回了手,大黑很鄙夷地盯著我,抬了抬下巴,相反,我現在倒有一種被狗挑釁的感覺,我又一次感覺自己受到了傷害。
多吉大叔咽喉不太好,睡到半夜常常咳醒,為了不打擾我休息,多吉大叔讓我和格桑睡在一起。我不會說藏語,而格桑也不會說漢話,兩個不是啞巴的啞巴只好一邊說著各自的語言,一邊講一邊猜,一邊用手指在半空或是床上亂劃,儘管這樣,雙方理解得都還是不夠透徹,常常說的是驢頭不對馬嘴,格桑有些洩氣,翻過身去便睡。
我睡不著,仰頭看屋頂,屋頂上的椽子一根一根的,我在想,如果以前沒有漢藏間的交流和融合,沒有兩個民族間文化的傳播,現在的藏民是否仍然在隨著牧草而遷徙?世界就是這麼奇怪,當初一點點的改變,在數百年後,竟會有意想不到的大變化。
格桑嘆了口氣,又翻過身來,他也睡不著,他想了半天,終於吞吞吐吐地說出一句話:「你,教,漢語,我!」
格桑想當兵,就必須學會說漢語,本來現在藏族學校裏也有教漢語這門課了,但在這個偏僻的地方,窮苦的孩子們大多不上學,他們每天放羊放牛,仍然過著類似遠古牧民的生活,多吉大叔雖然會些漢語,但他也不精通,平時更不會和格桑用漢語交談。
我很詫異格桑這句漢語是怎麼說出口的,他看見我臉上驚奇又歡喜的表情,知道是他那句漢語的功勞,就又生硬地說:「爸,教我,晚上。」
我摸了摸他的頭,笑著學他的話:「哥,教你,以後。」
格桑笑了,露出兩排小牙,一頭鑽到我懷裏。
半夜,忽然聽到村落裏的獒們一齊嚎叫起來,我和格桑都被驚醒了,格桑從被窩裏爬出來,跳到床中央,衝我齜牙裂嘴,又搖頭又擺屁股,做了個大灰狼的樣子,然後披上衣服就往院子裏跑去。
狼來了?
我腦子裏一熱,血就往頭頂上衝,腦子裏閃過凶殘的狼撕咬獵物的場景。
五、選擇和放棄
狼這種動物,我只是在電視上看到過,真正的狼還沒有親身領教,不知道會是一種什麼樣子。
我一個翻身跳起來,連衣服也沒披,就光著腳丫子衝到了院子裏。
多吉大叔不在家,獒吼第一聲的時候,他就提著油燈出去了,我和格桑跑到院門口向外張望,格桑和我一樣,也很興奮,不知什麼時候,他懷裏已經抱著那支槍,槍桿子被他一個晚上就給擦得鋥亮,在微薄的月光下閃閃發光。
多吉大叔回來了,格桑接過他手裏的油燈,興奮地用藏話喊:「狼呢?來了嗎?多不多?有幾條?」
多吉大叔咳了兩聲,告訴我們說,是隻被狼群拋棄的老狼,這隻狼以前可能是頭狼,現在受了傷,沒有吃的,就跑到了村子裏,聽到獒的叫聲,又嚇跑了。
大黑站在門口,一聲也沒叫,不用多吉大叔解釋我也知道,大黑是不屑於對這樣一隻可憐的狼吼叫的,她是一隻高高在上、目空一切的尊貴的獒,根本就沒把那隻被狼群拋棄的小混混放在眼裏,只有那些車前小卒才會在風吹草動的時候吠叫不止。
格桑興奮的心情還沒有平靜下來,他抱著那支槍,在院子裏作衝刺狀。
大黑慢慢地走到院門口,仰頭呼吸半夜清新的空氣,一邊欣賞天上的月亮,她的神情很專注而且莊重,就像是虔誠的穆斯林教徒在一條堅苦而漫長的道路上,遠遠地望見了聖地麥加。
格桑練了一會兒突刺,忽然說:「阿爸,我今天放羊的時候遇到狼了。」
「哦,幾條?」多吉大叔一邊抽他的旱菸,一邊漫不經心地問,草原上的孩子遲早會遇到狼,這沒什麼大不了的。
格桑坐了下來,把槍緊緊地摟在懷裏,眨著眼睛說:「一條,是母的,左後腿斷了,帶著兩隻沒睜眼的小狼。」
格桑說這些話的時候,語聲裏沒有對狼的仇恨,我反倒聽出了幾分憐憫,草原上的孩子純樸而天真,這個時候的他們還不知道仇恨,他們或許也不願意去區分誰是他們牧民的仇人,誰又不是。
多吉大叔沒有說話,他抽著自己的旱菸,抽得津津有味,一袋旱菸很快抽完,他敲了敲菸袋鍋子,才緩緩地說:「好幾年前了,雪天,我趕著羊到村裏的牧場上吃草,一群狼大概是餓瘋了,衝進了牧場,那時候,有兩家養了獒,還有幾支獵槍,狼群圍住了一隻待產的母羊,咬住了,死命往外拖,槍在響,獒也在叫,狼群只好撤退,有一隻狼被獒咬斷了腿,跑不快,拖得雪地上到處是血,頭狼走過去,在牠的咽喉上咬了一口……」
「阿爸,都是狼,頭狼為啥要咬同類?」格桑瞪大了眼睛,他還不明白什麼叫「優勝劣汰,適者生存」,他更不明白,要保存一個團隊的戰鬥力和至高榮譽,有時候,團隊的首領必須要殘忍而果斷地做出選擇。這,是狼的生存法則,格桑不是狼,更不會像狼那樣殘忍而絕情,他不能體會,所以也就無法明白。
多吉大叔知道我是聽明白了,就衝我點了點頭,轉頭問格桑:「要是你的羊群被狼襲擊了,後來狼跑了,很快又會回來,但是有一頭羊受了重傷,快死了,你必須趕快回到村裏,你說,你是要那頭快死的羊,還是要保住整個羊群?」格桑眨了眨眼,毅然地說:「都要,咱們牧民的衣食住行都在羊身上,咋能放棄呢?」
多吉大叔笑了,摸著格桑的頭,說:「傻孩子,都要?你保得住嗎?人啊,有時候就要學會放棄,到了那個時候,你不想放棄也不行,你看,狼都懂得這一點,咱們是人,兩條腿的還能比四條腿的笨嗎?」
不知道大黑是否聽得懂,她一直站在門口看月亮,我不知道,對於一隻獒來說,太陽、月亮,又有什麼好看的?或許,用獒眼來看人,人才是一種可笑的動物,整天忙忙碌碌,忘記了大自然的美,也不懂得欣賞大自然的美,就像一頭拉磨的驢,就知道整天轉啊轉啊……
我認定大黑有這種想法,是因為我終於看見大黑回了一次頭,而且是用一種嘲笑的眼神,盯了我兩秒鐘,我真的很懷疑,這隻巨大的獒是不是能猜透人類的想法,她是不是知道了我腦子裏在想的東西,所以要用這樣嘲笑的目光看我。
大黑很快轉過了頭,又往院子外望去,村落裏稀稀落落地坐落著牧民的土房子,這個村落的人不多,最多也就十幾戶,當天剛黑開始點燈的時候,村落裏的燈就像棋盤上的棋局,東一顆,西一顆,寥寥幾盞。